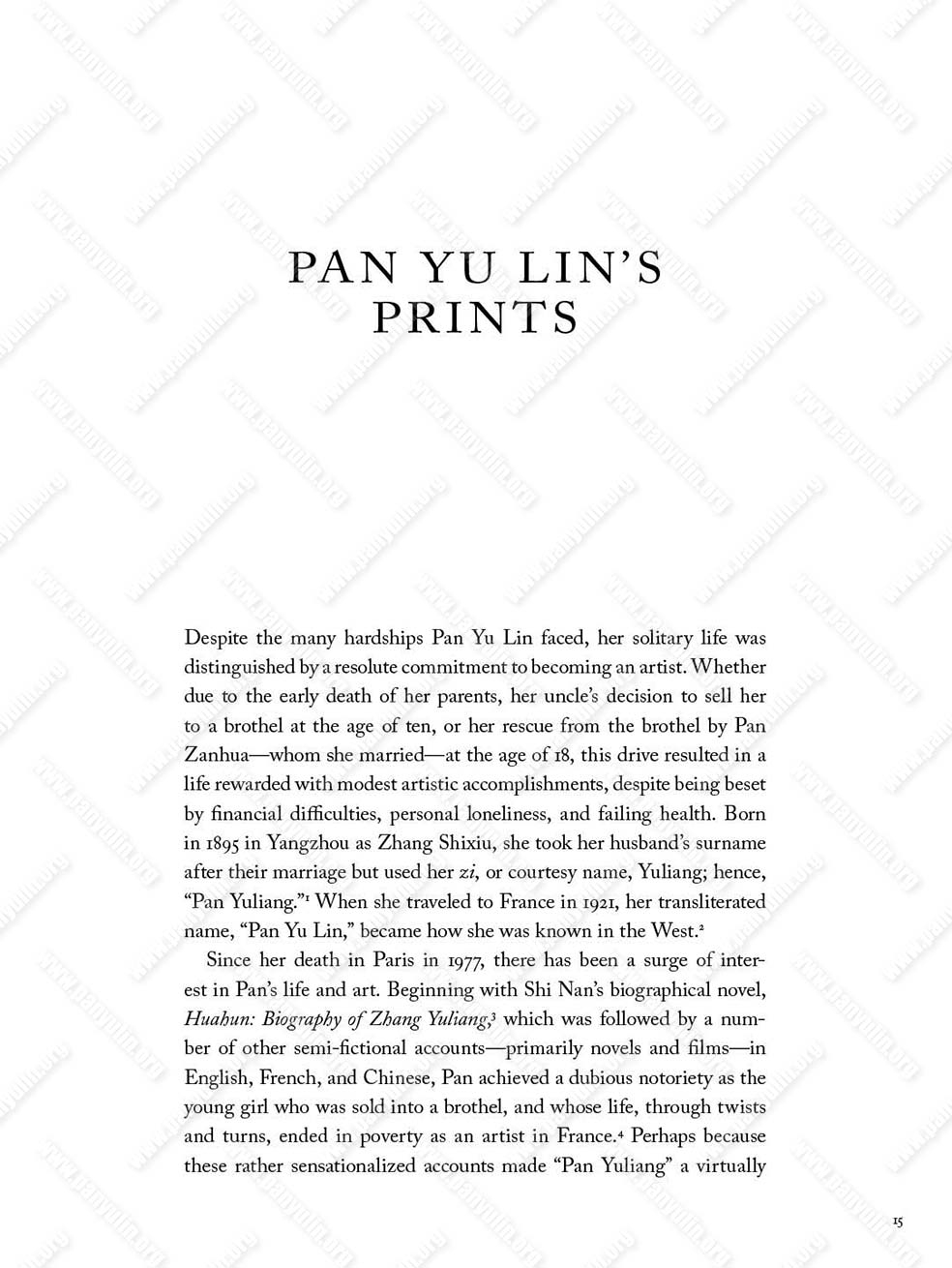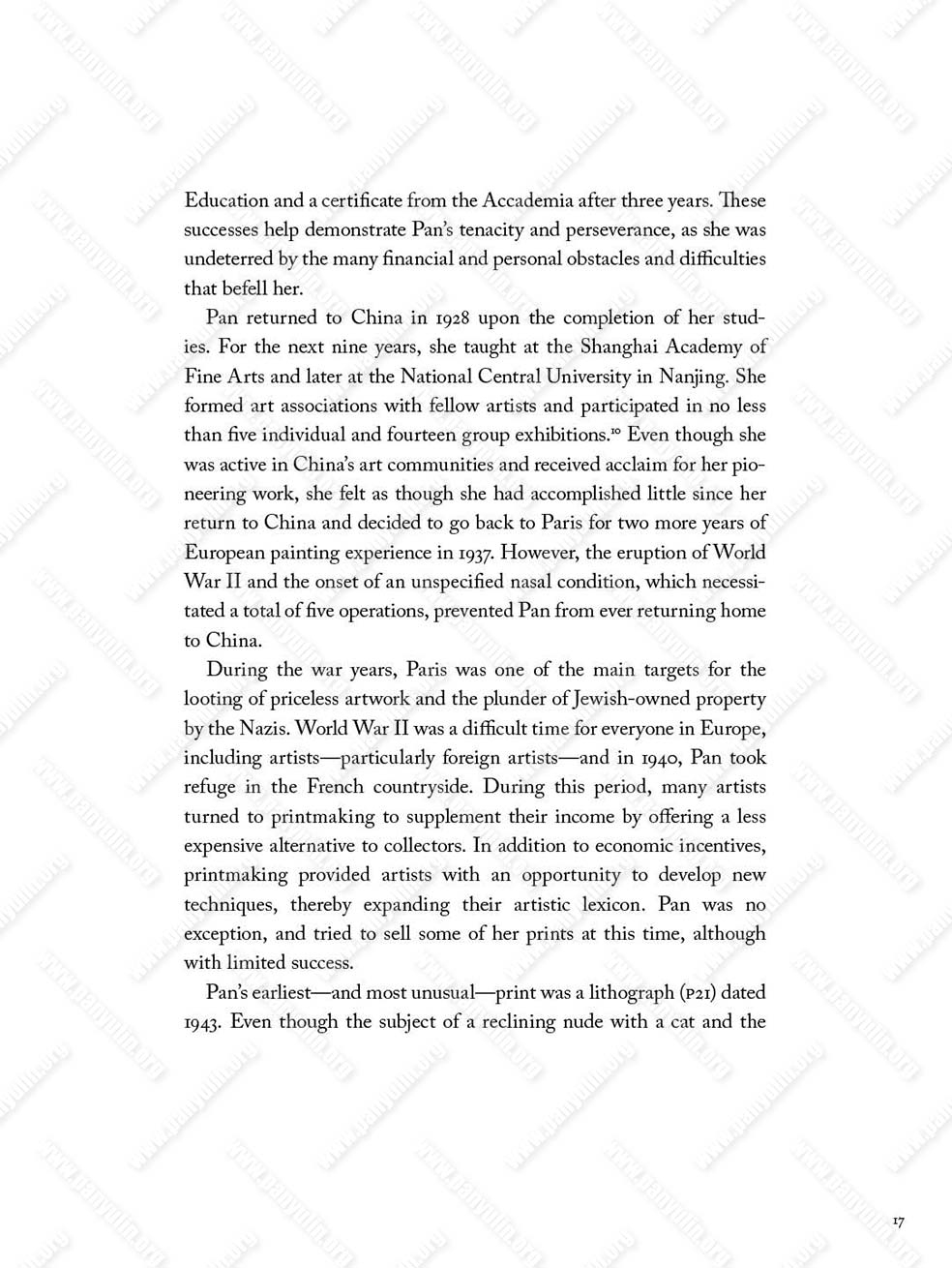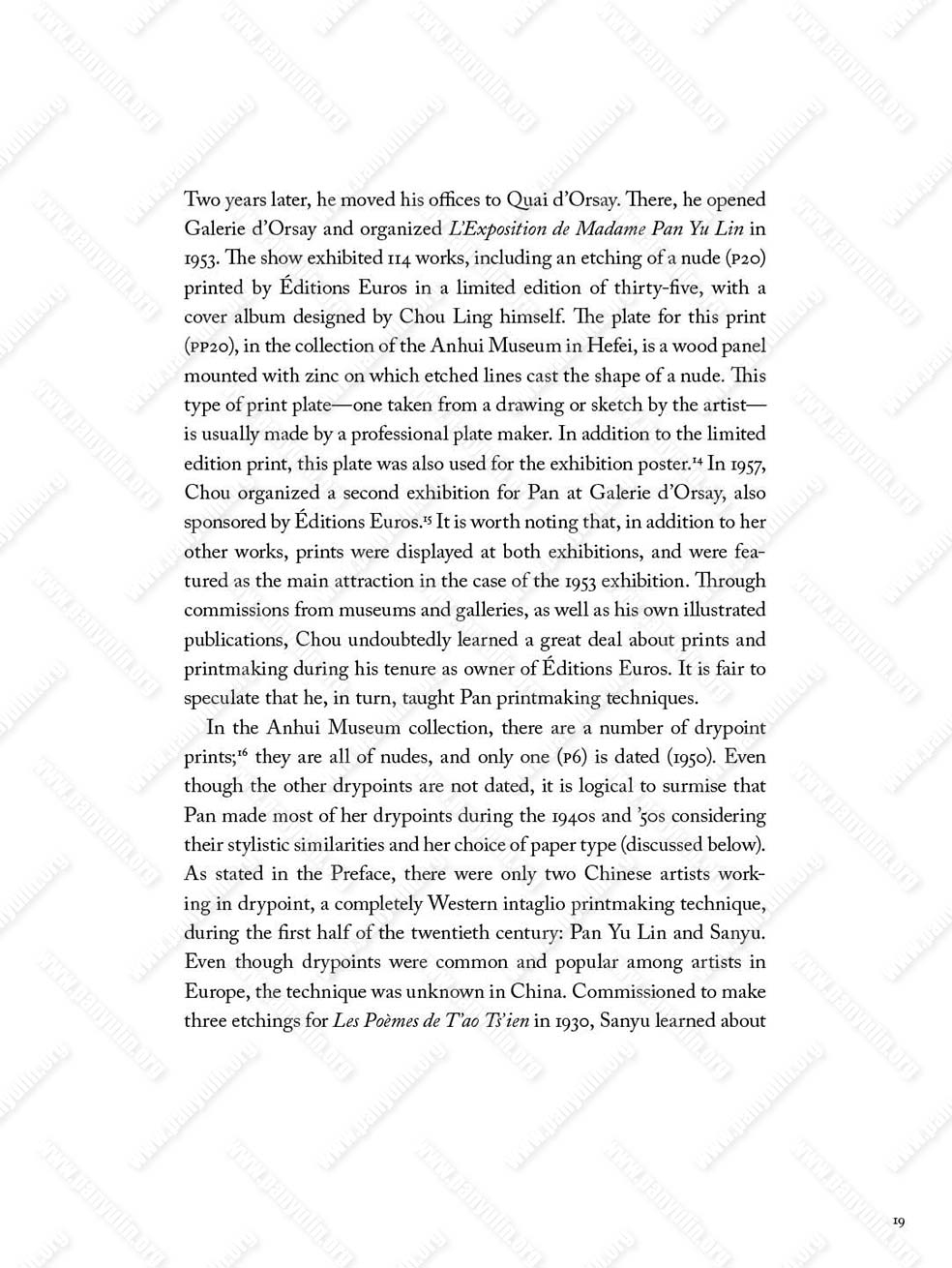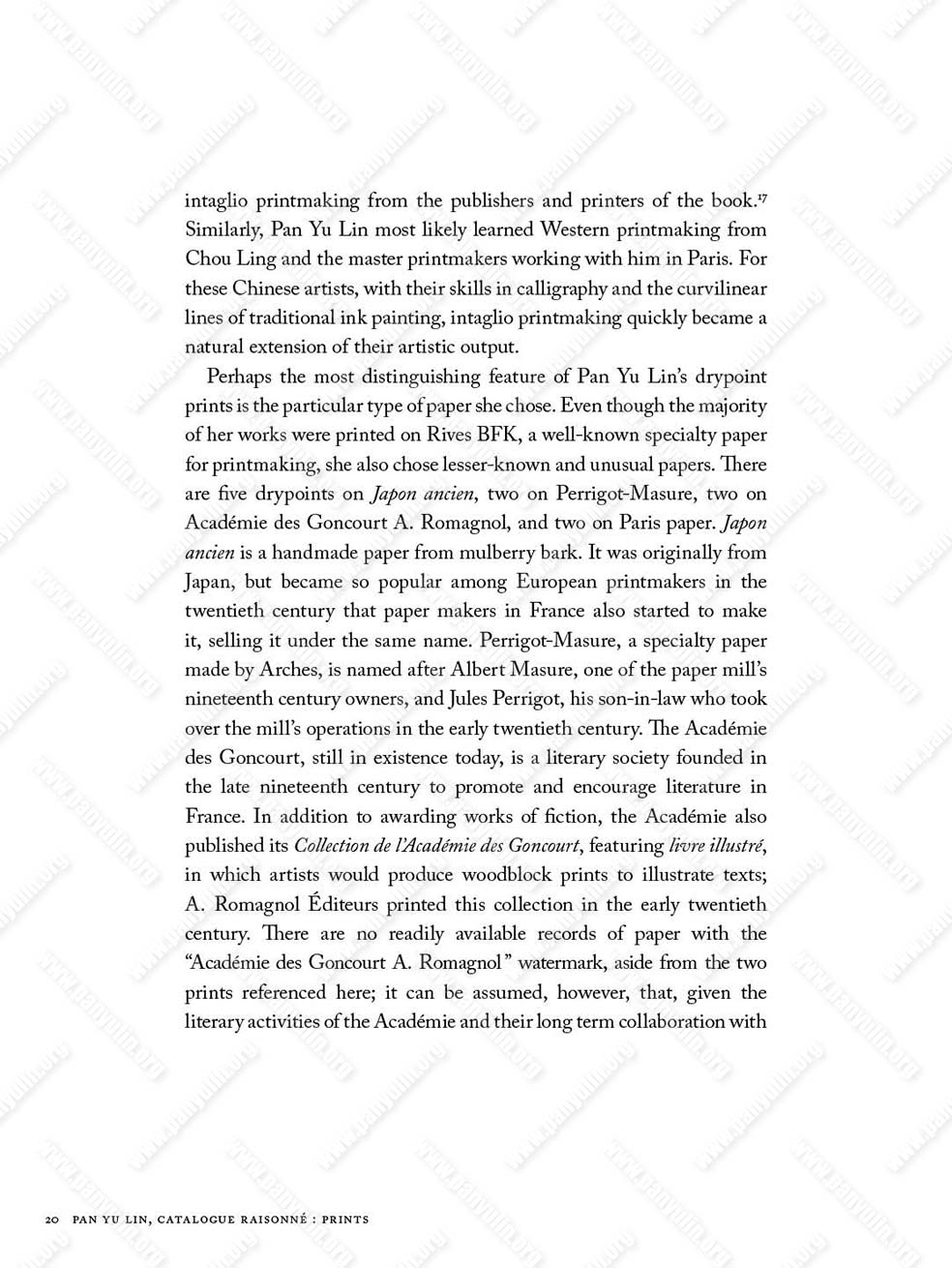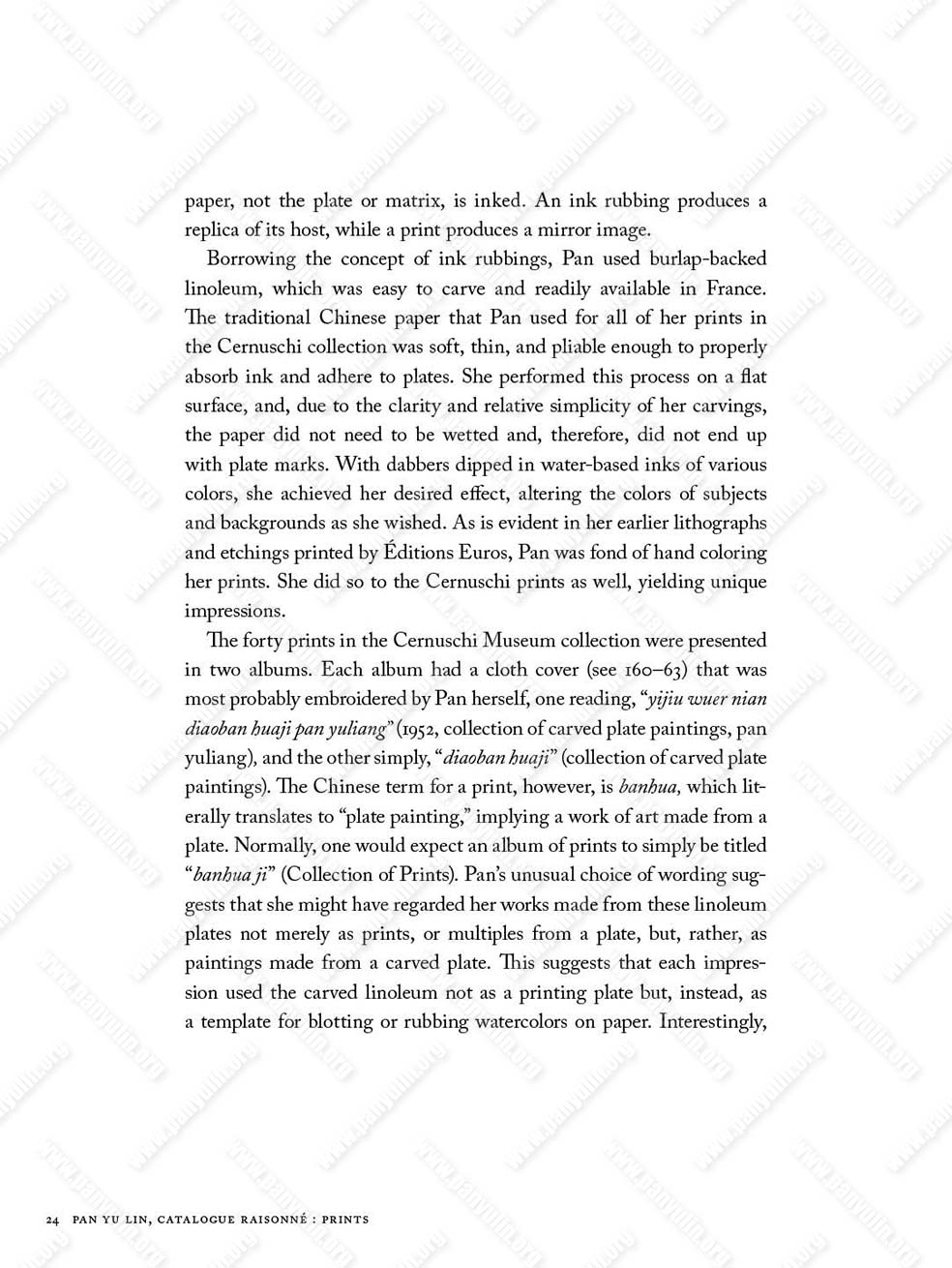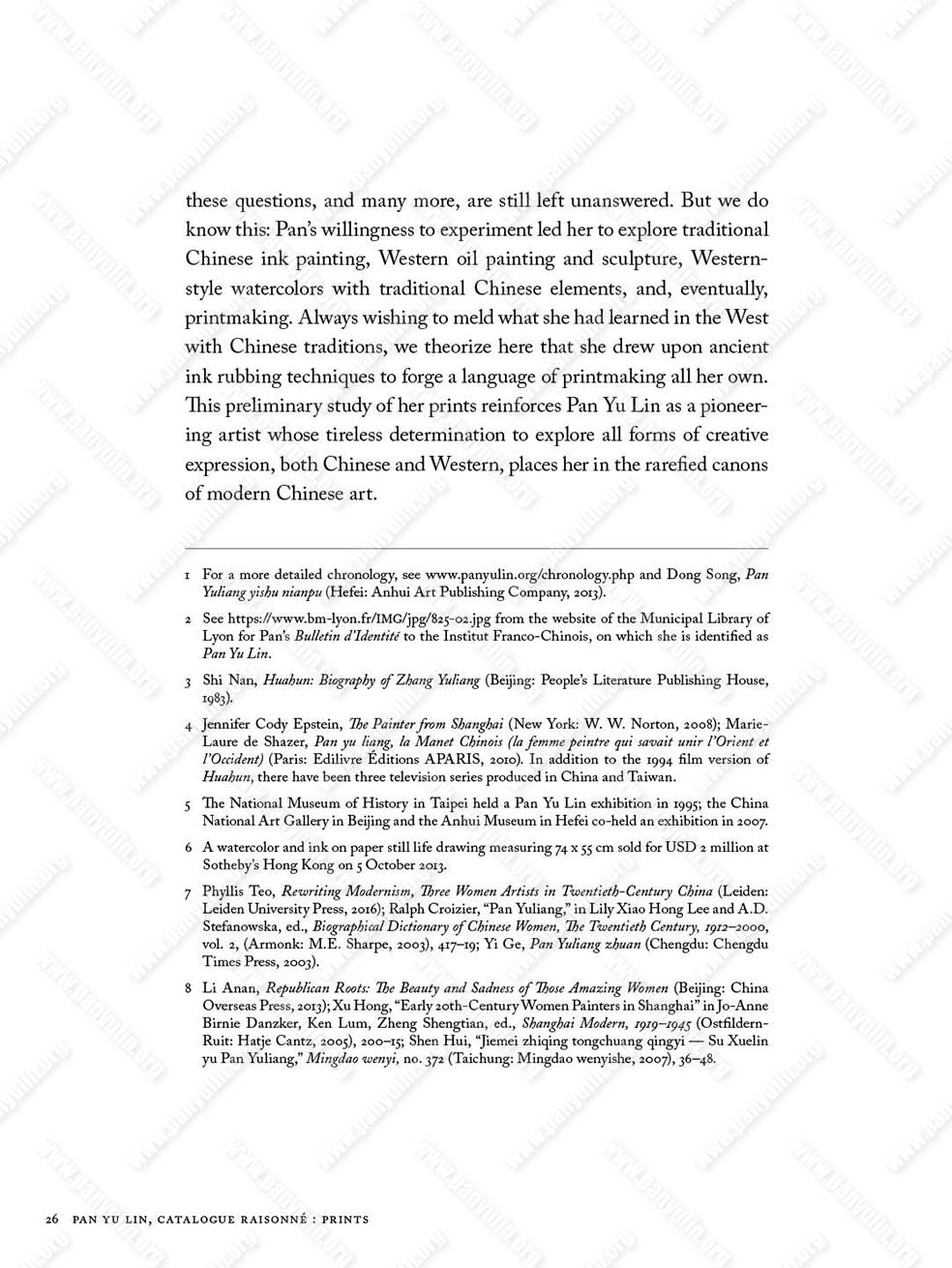潘玉良孤零的一生儘管面臨許多困難,但立志成為藝術家的決心,使她的人生卓然不同。不論是雙親早逝,或是十歲時被舅父賣入妓院,又或是十八歲時被後來與她結為夫妻的潘贊化從妓院贖回,這些經歷造就出她頗具藝術成就的人生,哪怕窘困的經濟、孤獨的生活以及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持續困擾著她。1895 年出生於揚州的潘玉良原名張世秀,婚後從夫姓潘,並改以字「玉良」行世,因此成了「潘玉良」;[1] 西方國家所知的則是她 1921 年初到法國時的譯名「Pan Yu Lin」。[2]
自 1977 年潘玉良在巴黎辭世以來,愈來愈多人對她的生平與藝術產生興趣。從石楠筆下的傳記式小說《畫魂——張玉良傳》,[3] 到後來一些多為小說或電影形式的英文、法文及中文半虛構作品,潘玉良漸漸被傳知成一位落入青樓的年輕女子,歷經曲折起伏的人生,最後在法國成為一個窮困的藝術家。[4] 或許是因為這些頗為煽情的故事將「潘玉良」變成了一個在亞洲幾乎家喻戶曉的名字,以致於中國和臺灣的博物館相繼舉辦大型回顧展,將她的藝術介紹給廣大好奇的民眾;[5] 國際拍賣公司也藉此機會將需求量大增的潘玉良畫作,以這十年來急速飆漲的價格,提供給日益眾多的收藏家。[6] 除了展覽圖錄以及介紹潘玉良及其藝術的專論外,也有不少研究專門探討潘玉良作品中的革新性本質——尤其是她融合東西藝術傳統的獨特方式——如何讓她躋身為近現代中國藝壇的重要先驅。[7] 另外也有部分研究聚焦於潘玉良身處男性主導世界中的女性藝術家角色,以及她如何與其他同時期的中國女性,如方君璧和蘇雪林,一同找到自己的道路。[8] 近來也有愈來愈多的學術研究著重於「裸女」在潘玉良藝術創作中的定位,以及這個西方題材對她的重要性,因這與潘玉良以女性角度所看到的自我形象有所關聯。[9]
潘玉良終其一生都展現著想要成為傑出藝術家的頑強決心。1920 年進入上海美專的隔年,潘玉良即被迫退學,原因是有學生發現她曾在妓院工作,而校方為平息事端所致。所幸同年她考進里昂中法大學,並於 1921 至 1923 年間在里昂國立高級美術學院修課。在這段期間,儘管和里昂兩所學校的課程有所衝突,她依然經常前往巴黎隨呂西安.西蒙學畫,隨後也進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進修兩年。1925 年她赴羅馬美術學院學習繪畫與雕塑,並獲得義大利教育部提供的年度津貼,三年後取得該學院頒發的修課證明。從這些成績中,我們看到了潘玉良的堅韌與毅力,經濟和生活上的阻礙與困難並未使她卻步。
潘玉良於 1928 年學成返國,接下來的九年期間先後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以及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她與其他藝術家共同成立過一些藝術社團,並參加不下五次個展以及十四次聯展。[10] 雖然在中國藝術圈表現活躍,其先驅之作也獲得高度評價,潘玉良卻深感回國後學無所成,於是在 1937 年決定回到巴黎深造兩年,以學習歐洲繪畫。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導致前後五次手術的不明鼻疾,令潘玉良終身再未回到中國。
二戰期間,巴黎是納粹掠奪藝術珍品及猶太人財產的主要目標之一。這個時期對每個身處歐洲的人來說都非常艱難,包括藝術家——特別是外籍藝術家,也致使潘玉良在1940 年來到法國鄉間避難。在這段期間,許多藝術家改作版畫,提供收藏家一個價格較為低廉的選擇,並藉以維持生計。除了經濟上的誘因外,製作版畫也讓藝術家有機會發展新的技法,藉此拓展藝術語彙。潘玉良在當時也曾經嘗試銷售一些版畫作品,但成效有限。
潘玉良最早也最不尋常的版畫是一幅 1943 年的石版作品(P21)。雖然側臥裸女與貓這樣的主題,以及加強描繪織品細節的手法,使人聯想到她的油畫及彩墨作品,但「123」這樣一個特殊的總版數,以及「Gyoku」這個署名,卻不太容易被解釋。「Gyoku」(日文的「玉」)可能是她名字的簡稱,而以日文署名表示這幅版畫可能是受託為日本市場所製。潘玉良在 1930 至 1940 年代是中國留法藝術學會的成員,因而認識了身兼藝術家、藝術史學者與評論家,同時也是中國留法藝術學會會長以及中華民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的周麟(1915–1970)。除了這些官方身分外,周麟也撰寫藝術相關文章,或將中文譯為法文版本,並經常自行配上插圖。[11] 他同時積極向法國收藏家推銷中國藝術家,[12] 例如張大千和傅抱石;更和其他中國藝術家維持友好關係。透過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以及與這些藝術家的連結,周麟和日本藝術市場也有所往來,可能因此為潘玉良促成了這幅版畫的委製。由於這幅作品是石版畫,潘玉良在版畫師的協助下即可輕易完成(石版是一種最接近於素描的製版方式,不需特別學習如何蝕刻或雕刻畫版)。這幅版畫的最後一個奇特之處在於,身為一個沒有經驗的新手石版畫家,潘玉良選擇在織品及靠枕上以手工繪製裝飾性的細節來強化每幅作品,這也是她在油畫和素描作品中的一大特色。
1950 年,周麟在巴黎成立了「歐洲出版社」,由法籍妻子歐黛特.赫茲出任董事。歐洲出版社專門印製高品質藝術圖錄,最知名的客戶是和周麟有著密切合作關係的巴黎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13] 兩年後,周麟將出版社搬到奧賽碼頭,同時開設了「奧賽畫廊」,並於 1953 年舉辦「潘玉良畫展」。該展覽共展出一百一十四件作品,包括由周麟親自設計封面,歐洲出版社限量印製三十五版的一幅蝕刻裸女(P20)。這幅作品的畫版(PP20)收藏於合肥的安徽博物院,是將蝕刻好的鋅版翻鑄成裸女輪廓狀,再鑲嵌於木板上。這種由藝術家素描或速寫翻製而成的畫版,通常是由專業的製版師傅製作。除了印製限量版畫外,這個畫版還用於印刷展覽海報。[14] 1957 年,周麟在奧賽畫廊為潘玉良舉辦第二次展覽,也是由歐洲出版社贊助。[15] 值得注意的是,兩次畫展除了潘玉良的其他作品之外,都展出了版畫,1953 年的展覽更是以版畫為主角。周麟在經營歐洲出版社的期間,透過博物館和畫廊的委製,以及自家插畫書的出版,必定學到了許多版畫以及製版的相關知識,我們也因此推測他教導了潘玉良製版技術作為回報。
安徽博物院收藏的潘玉良版畫中有許多直刻版畫,[16] 主題都是裸女,而且只有一幅(P6)簽具了日期(1950)。儘管其他的直刻版畫均未標註日期,但是由風格相似度以及紙張的選擇(見下文探討)來看,我們合理地推測潘玉良大部分的直刻作品創作於 1940 至 1950 年代。在前言中提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只有潘玉良和常玉兩位中國藝術家採用直刻這種純西式的凹版雕刻技法。雖然直刻在歐洲非常普遍且受歡迎,但對中國人來說卻完全陌生。常玉 1930 年受託為《陶潛詩選》製作三幅蝕刻版畫,從出版商和印刷師傅身上學習到了凹版製作技巧。[17] 同樣地,潘玉良大概也是向周麟以及他所配合的巴黎版畫製作大師學習製作西式版畫。對這些中國藝術家來說,有了書法以及傳統水墨畫流暢線條的技巧為基礎,凹版畫很快就變成一種自然延伸而成的創作方式。
潘玉良的直刻版畫最與眾不同的特色,大概就屬她所選用的紙張。雖然她大部分的作品都印在 Rives BFK 這種知名的版畫專用紙上,但也有部分選用了一些較不為人知、不常見的紙張。潘玉良有五幅直刻作品印在 Japon ancien 紙上,兩幅在 Perrigot-Masure 紙,兩幅在 Académie des Goncourt A. Romagnol 紙,以及兩幅在巴黎紙。Japon ancien 是一種以桑樹皮製成的手工紙,最初源自日本,二十世紀時非常受到歐洲版畫業界的歡迎,於是法國的造紙廠也開始以相同的名字生產並販售這種紙張。Perrigot-Masure 是阿契斯造紙廠生產的專用紙,以該廠十九世紀負責人之一的阿勒貝.馬敘(Albert Masure),以及二十世紀初期接掌紙廠的女婿居勒.沛利構(Jules Perrigot)命名。龔固爾學會(Académie des Goncourt)成立於十九世紀晚期,是在法國推廣並鼓勵文學的社團,現今仍然存在。除了獎勵小說創作外,龔固爾學會也出版書選,在二十世紀初由侯瑪紐出版社(A. Romagnol Éditeurs)所印製,其中包含了插畫書,也就是由藝術家創作木版插圖來搭配文字內容的出版品。關於帶有「Académiedes Goncourt A. Romagnol」浮水印的紙張,除了本書收錄的兩幅版畫之外,尚未見其他相關資料。然而從龔固爾學會的文學活動及其與侯瑪紐的長期合作關係,我們可以假定這種帶有雙方名字浮水印的紙是為特殊用途而生產,而非供日常商業使用。市面上有數種帶不同樣式「Paris」浮水印的手工版畫紙,但潘玉良為兩幅直刻版畫所選用的這款巴黎紙,我們則一無所知。沒有任何資料記載潘玉良是如何取得這些不同的特殊紙張,我們也不知道她和哪些版畫印製廠合作。即便如此,潘玉良很自然地選用直刻版畫來表達「裸女」這個她在 1940 至 1950 年代格外投入的題材。此外,為了達到她對完美的獨特要求,潘玉良蒐羅最稀有、最專門的紙張(可能在周麟的協助下)來完成她的創作。除了安徽博物院的藏品外,目前沒有其他已知的直刻版畫。
1977 年 7 月,時任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的葉賽夫,為四位中國女性藝術家舉辦「中國當代藝術家四人展:潘玉良、林藹、吳似丹、成慧」。潘玉良為本展選送了五幅油畫、十七幅素描和水彩、六件雕塑、兩件石膏版,以及四十幅版畫,[18] 其中的版畫大多是裸女,再次印證這個題材對潘玉良的重要性;而不尋常的版畫製作方式,也凸顯了她身為藝術家的複雜性。1982 至 1994 年間擔任賽努奇館長的瑪麗—泰瑞絲.波柏(1929–2011)曾經形容「這些裸女版畫從灰階演變成彩色」。[19] 這些版畫出自同一個畫版,卻在色調、質感,以及顏色上展現出如此豐富的變化,因此僅能被視為孤版。當賽努奇的版畫和安徽博物院的橡膠畫版配對上後,另一個更令人不解的疑惑出現了:印製版畫通常是將墨水塗佈在畫版上,然後以人工或機器壓印在紙上,產生出畫版的鏡像。然而安徽博物院的這些畫版,和賽努奇的版畫卻是相同方向。
我們從製版技法中找到一種可能的解釋,那就是將剛從畫版印出的版畫,隨即印到另一個表面——通常是紙上。在這種情況下,第一幅版畫是所謂的「cognate」。也就是說,當第一幅版畫的墨還未乾前,就將其轉印到第二張紙上,創造出鏡像的鏡像,最後得到的版畫看起來就會和畫版一模一樣。通常會採用這種方式,是因為有些難以被刻畫在堅硬表面上的特殊紋理效果,可以輕易地在紙本 cognate 上達成,然後再印製成最終成品。這個方法雖然從技術層面解釋了如何印出與畫版相同方向的版畫,卻無法說服我們為什麼一個藝術家要捨近求遠,來創造這種橡膠版印刷原本就可簡單達成的漸變色階效果。
不論是技法上或是主題上,潘玉良都偏好在作品中加入傳統中國元素,這為她的孤版提供了另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中國的拓印傳統。石材、金屬和陶片上的圖像或銘文拓印,是一種透過精確複製來保存歷史的方式,在中國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當珍貴遺跡不復存在,最後傳世的往往僅有拓片。拓印一直以來是保存歷史及藝術史料的關鍵方式,其重要性不可被輕忽。[20] 雖然無法確切肯定,但是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潘玉良知道這項傳統,並藉此方式來創作賽努奇的這些孤版。
傳統拓印選用的紙張通常薄且強韌,足以承受墨水持續拍印的力道;此外質地也要柔韌,以便貼合刻面並產生更好的墨水吸附效果。在進行古碑拓印時,由於大多時候碑碣仍立於原址,且過於龐大無法移置平放,因此紙張必須完全打濕,才能穩固地貼附於碑碣上;也因為包覆在碑碣或雕刻上的紙是濕的,揭下的拓片乾燥後往往都會留下類似版痕的痕跡。待紙張妥善地固定在雕刻表面後,就可以視版體的性質以及藝術家的喜好,選擇不同大小及形狀的拓包來上墨。最常見的拓包呈倒置蕈菇狀,蕈蓋用來蘸墨,蕈柄充當手把。拓包通常以絲或棉布包裹羊毛、棉花或其他柔軟吸墨的材料,吸附墨水後,就可以小心地拍打於紙的表面,創造出黑色的背景,以及未上墨處的白色刻線及圖案。如果版體是陽刻,就會呈現相反的效果,也就是描繪圖案或文字的凸起部分會被拓印出墨色,背景則為未上墨的白色。不管最後呈現的是哪一種效果,拓印這種方式是在紙張上蘸墨,而不像版畫是在畫版或版體上蘸墨,其產生出的圖案也和版畫相反。拓片如實複製版體,版畫則是造出鏡像。
潘玉良借用了拓印的概念,並使用容易雕刻且在法國便於取得的麻底橡膠版。賽努奇館藏版畫所選用的宣紙薄軟柔韌,能夠適度地吸附墨水並貼合於畫版。由於潘玉良是在水平的平面上進行拓印,再加上她的雕刻清晰且相對簡單,因此不需要將紙打濕,也就沒有留下版痕。潘玉良用拓包蘸取各色水性顏料,隨心所欲改變主體以及背景的顏色,達到她理想中的效果。從歐洲出版社為潘玉良印製的石刻以及蝕刻版畫,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她喜歡在版畫上手繪著色,賽努奇收藏的這些版畫也是如此,從而創造出孤版。
賽努奇的四十幅版畫分別裝訂成兩本畫冊,均為布質封面,應該是潘玉良親自在封面上繡字, 一本題「一九五二年」、「雕版畫集」、「潘玉良」,另一本僅題「雕版畫集」(見頁 160–163)。「版畫」顧名思義是以畫版所印製的畫作,正常來說,集結版畫的書冊稱「版畫集」即可。潘玉良選用特殊的詞彙,顯示這些橡膠版印製出的作品,對她來說不僅僅是版畫或是用畫版印刷出來的複本,而更像是藉助畫版所創作出的畫作;也就是說,這些橡膠版不是用來當作印刷版,而是做為可將水彩塗附或拓印到紙張上的模版。有意思的是,這些作品可以同時被視為版畫和畫作,也可以兩者皆非。潘玉良 1953 年為奧賽畫廊個展所創作的限量版畫,周麟稱之為「畫作」(peinture),意味著雖然是蝕刻作品,但手繪細節讓它們成為畫作;不過 1977 年潘玉良逝世前不久在賽努奇所舉辦的展覽上,她的作品被描述為「版畫」(gravures),而潘玉良當時對此顯然並無異議。拓片終究是由版體所產生,因此仍舊算是版畫的一種。
賽努奇展覽後三個月,潘玉良不幸辭世。瑪麗—泰瑞絲.波柏回憶道,「她沒忘記要將兩本橡膠版畫集捐給我們……正式的捐贈在 1978 年,多虧她的受遺贈人,也就是她的表親王守義。」[21] 除了賽努奇之外,目前尚未發現其他的孤版;無獨有偶,除了安徽博物院的藏品外,也沒有任何已知的直刻版畫。令人好奇的是,安徽雖藏有同一幅版畫的不同版次,但僅三幅有編號:P20(蝕刻版畫,總版數 35)、P21(石版畫,總版數 123),以及P22(蝕刻版畫,總版數 200)。我們不清楚奧賽畫廊曾售出哪些版畫,但未加註編號,顯示潘玉良似乎沒有特別打算銷售這些直刻或孤版。這是否只是她的版畫習作,抑或是一位身處巴黎的中國藝術家艱鉅旅程中的另一次探索,我們不得而知。
潘玉良如何得知並取得這些罕見的手工紙來製作她的直刻版畫?為什麼石版作品上署名「Gyoku」,且總版數為特別的「123」?她究竟是如何用橡膠版做出賽努奇的那些孤版?當這些問題還有許許多多其他問題都尚未得到解答之前,毅然出版這本畫冊確實令我心有不安。但我們知道的是潘玉良樂於嘗試,探索範圍遍及傳統中國水墨畫、西方油畫與雕塑、帶有傳統中國元素的西方水彩,最後來到版畫。潘玉良一心想將西方所學與中國傳統融合,因此我們推論她採用了古老拓印技法,鍛造出屬於她自己的版畫創作語言。這份對潘玉良版畫的初步研究,再一次說明了潘玉良是位先驅藝術家,她不懈地探索東西方各種創作表達形式,更奠定了她在近現代中國藝術史上的地位。
1. 更詳細的年表,請見 www.panyulin.org/chronology.php 以及董松,《潘玉良藝術年譜》(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13 年)。
2. 里昂市立圖書館網站上所刊載的潘玉良中法大學註冊登記表,姓名是「Pan Yu Lin」;檔案請見 https://www.bm-lyon.fr/IMG/jpg/825-02.jpg。
3. 石楠,《畫魂——張玉良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
4. 珍妮佛.寇迪.艾普斯坦,《來自上海的畫家》(紐約:諾頓出版社,2008 年);瑪麗—洛禾.德.沙澤,《潘玉良,中國的馬內(融合東西的女畫家)》(巴黎:艾迪利弗出版社,2010 年)。除了 1994 年電影版的《畫魂》外,中國及臺灣也製作了三部電視劇。
5. 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曾於 1995 年舉辦潘玉良畫展,北京首都博物館和安徽省博物館(今安徽博物院)則是在 2007 年合辦「潘玉良畫展」。
6. 一幅 74 x 55 公分的彩墨靜物畫於 2013 年 10 月 5 日在香港蘇富比以二百萬美元售出。
7. 張慧玲,《改寫現代主義:二十世紀中國的三位女藝術家》(萊頓:萊頓大學出版社,2016 年);羅夫.克洛濟爾,〈潘玉良〉,蕭虹、斯帝法諾斯卡合編,《中國婦女傳記辭典,二十世紀卷,1912–2000》第二冊(阿蒙克:夏普出版社,2003 年),頁 417–19;伊戈,《潘玉良傳》(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2003 年)。
8. 李安安,《民國紅顏:那些奇女子的美麗與哀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 年);徐虹,〈二十世紀初期上海女畫家〉,喬安.伯尼.丹斯柯、林蔭庭、鄭勝天合編,《上海摩登:1919–1945》(奧斯特菲爾德爾恩—茹易:哈特耶.康茲出版社,2005 年),頁 200–15;沈暉,〈姐妹之情,同窗情誼——蘇雪林與潘玉良〉,《明道文藝》第 372 期(臺中:明道文藝社,2007 年),頁 36–48。
9. 艾莉莎.帕克,〈論藝術中的現代性:潘玉良(1895–1977)與跨國現代性〉(安娜堡:密西根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13 年);艾爾莎.法夫洛,〈潘玉良藝術中的裸女〉(倫敦: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藝術與考古學碩士論文,2006 年)。
10. 完整參展清單,請見 www.panyulin.org/records.php。
11. 範例請見周麟,《中國人的美德》(巴黎:年輕的命運女神出版社,1947 年);周麟,《傳統式中國當代繪畫》(巴黎:歐洲出版社,1949 年),內附作者創作八幅插圖;周麟,〈中國當代雕塑〉,《中國當代繪畫展》(展覽圖錄,巴黎: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1946 年),頁 33–5。
12. 存放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亨利.皮爾.侯謝收藏之常玉作品清單中,有些畫作條目旁註記「周麟退回」,顯示周麟曾試著向巴黎的收藏家推銷常玉作品,並活躍於藝術市場。另見瑪麗—泰瑞絲.波柏,〈賽努奇博物館與中國當代繪畫〉,《法國東方聯誼會刊》第 44 卷(巴黎:法國東方聯誼會,1999 年冬),頁 14。
13. 波柏,同上,頁 12。歐洲出版社為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印製展覽目錄的範例,請見《張大千畫集:巨荷四聯屏展圖錄》(1961 年 5 至 6 月),以及《凌叔華之十四至二十世紀書畫收藏展》(1962 年 11 月至 1963 年 2 月)。
14. 范迪安編,《潘玉良全集 8.文獻卷》(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15 年),頁 63。
15. 范迪安編,同上,頁 65–66。
16. 關於製作直刻版畫的簡介,請見衣淑凡,《常玉版畫全集》(臺北:財團法人立青文教基金會,2017 年),頁 38–39。
17. 衣淑凡,《常玉版畫全集》,頁 42–44。
18. 葉賽夫,《中國當代藝術家四人展:潘玉良、林藹、吳似丹、成慧》(巴黎: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1977 年),頁35–66。
19. 波柏,同上,頁 14。
20. 有關傳統中國拓片的詳細歷史及研究,請見肯尼斯.斯達,《黑老虎:中國拓片入門》(西雅圖和倫敦:華盛頓大學出版社,2008 年)。
21. 波柏,同上,頁 14。王守義(1898–1981)並非潘玉良的表親,但卻在她的一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王守義是河北省高陽人,1920 年響應政府「勤工儉學」計畫前往法國,後來在巴黎自己開設的餐廳中結識潘玉良,兩人遂成為好友。王守義為潘玉良提供了經濟以及生活上的支持。潘玉良死後,王守義負責保管她的作品,直到它們被運回中國。王守義將潘玉良葬在他為自己所買的墓地,他死後也葬在同一處,和潘玉良為伴。